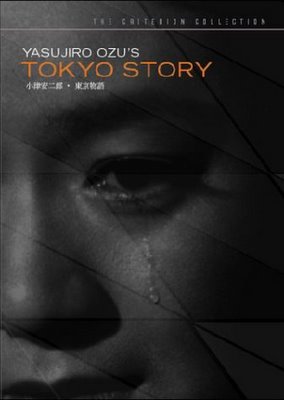
2006.01.01 中國時報 人間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0+11051301+20060101,00.html
小津的世界 早春、晚春、麥秋OZU
李歐梵 (20060101)
記得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看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終場時我發現大部分觀眾都是眼淚汪汪地離場,那是在一座大學城──普林斯頓,觀影者大多是學生和教授,是一個很「世故」(甚至相當「勢利」(snobbish)的地方,然而大家卻被小津電影中純真的世界所感動。如果說當今世界仍然存有「普世價值」的話,小津應該是「家庭」價值的歷史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影史上最動人的見證。
最近幾年,也許因為我年歲日增,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鍾愛小津的電影。日前某晚又和妻子同看他的「早春」,這是他一九五六年出品,繼「東京物語」(一九五三年)後的傑作,也許沒有後者那麼感人,而且片子全長一百四十四分鐘,可能也創下小津最長的影片的紀錄,但是我一口氣看到底,一點也不覺得沉悶。為什麼?
許多影評人都說過:小津的作品故事越來越平淡,場景就是那幾個:火車、東京的辦公大樓、日本式的住屋、人物都往往坐在室內的「榻榻米」上(因此鏡頭也大多從這種三呎高的坐姿拍攝)──酒吧間中的幾張凳子、一個吧台,最多再加上幾個吃飯的小房間……。小津的鏡頭也只有那幾個:開場的場景往往是火車疾行,接著是一兩個外景的空鏡頭,然後就進入室內,家裡的人開始起身、吃飯、談話、上班……。甚至小津影片中的對白也極平庸簡單,往往還夾雜了不少「空話」,譬如「啊,是嗎?」「嗯!」「是的」,當然更多「早安」「謝謝」之類的日常招呼詞。幾乎所有的影片都沒有高潮,「早春」尤其如此,那位男主角的表情永遠是一臉的無奈,正像其他影片中的原節子說話時永遠是一臉的微笑一樣。還有那位在小津影片中從年輕演到老(真實年齡)的笠智眾,一直老到演「東京物語」和「晚春」中的老祖父和爸爸。最妙的是「麥秋」幾乎成了「晚春」的翻版和回應,場景幾乎一樣,只把男女主角的角色對調就行了,都是為了結婚或不結婚。
●「結婚」主題
記得我多年前在研究院學日文時,最先學到的一個名詞就是「結婚」,這也是小津電影中的永恆主題,然而他自己卻一生未娶,而且事母至孝,他母親死去不久,小津也隨之去世,所以他的影片中母親的形象──和由此而衍生的家庭主婦的形象──更多。然而在他的電影世界中,男女仍然是分開的,在酒吧喝酒的永遠是男士,如果女性插足男性世界的話(如「早春」中綽號金魚的女同事),一定居心不良,變成破壞家庭的一份子。在辦公室裡,男女各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授受不親,即使一起去郊遊,男女之間也不踰矩,更沒有什麼兩性吸引的火花。
在小津的世界中,似乎沒有任何身體的慾望,只有生活。難怪美國和歐洲的導演們對小津只有讚羨,卻學不到他的精髓:德國的溫德斯(Win Wenders)應算是最崇拜小津的人,但他自己的電影風格仍然缺乏「小津味」。侯孝賢在多次否認受小津影響後,終於承認在鏡頭的運用上受到小津的啟發,但從「童年往事」到「悲情城市」,侯孝賢影片中的家庭還是比不上小津作品中的恬靜和樸素。
有的影評家說:這就是小津電影中特有的「禪」味!我不完全同意。我覺得小津從頭到尾都是「入世」的,甚至很世俗。也許我們從小津自己說的一段話中得到一點啟發:
「我沒有汲汲於交代故事,反而留下許多空白……,我想,這些空白,其餘韻或將更深遠。」
對我來說,這句話中最值得深思的就是「空白」和「餘韻」這兩個名詞。「空白」是一種形式上的美學和哲學,談論的人很多,餘韻應該是空白的副產品,但我卻將之視為對等物。且讓我先從餘韻(回味)說起。
也許「餘韻」和「餘味」甚為相似,但也有些許不同。小津的作品中,至少有兩部影片的名字帶有「味」覺:「茶泡飯之味」和「秋刀魚之味」,但只有一部與音韻有關係:「東京合唱」(一九三○年,我沒有看過)。然而,每當我看完一部小津的電影在回味時──甚至在觀影過程之中──都感受到不少「餘韻」。
●歌韻場面
最令我感動的歌韻場面,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鏡頭背後聽到的小學生或中學生合唱。也許我嗜愛音樂太深,每聽到那股餘韻繞山谷的合唱,就會想到我初到台灣時在新竹中學唱的歌,起初時聽起來,的確有點「日本味」,但原曲往往不是來自日本,而是德國:例如改編自舒伯特的「菩提樹」。這類音樂是我少年的精神食糧,想對小津個人更是如此,我甚至可以大膽地推斷:小津和他那一代日本人,經過二次大戰(他也被召入伍)的殺戮後,如何仍能保存一點人性?音樂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德國的藝術歌曲尤然。此中的文化原因有待查證,但這種「餘韻」似的情操,倒是在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的一場戲裡得以發揮,也就是片中引用的德國民歌「羅瑞萊」(Loreilei),然後接著是談到明治時期日本年輕人因為追悼美感而跳崖自殺的故事。
在大自然中聽到歌唱的音韻──特別是學生郊遊時唱的歌──往往令年長的人有所回味,即使不主動地聽,音畫對位的效果卻會觸動對人生旅程的感傷,所以老年夫婦在沙灘堤上望海無言(「東京物語」),一片失落之情,然後老頭子對他老伴說: 「該回家了!」於是她也回答:「噢!」(我看到此,早已熱淚盈眶)。於是,老父對女兒說:「你該結婚了!」女兒說:「不,我要永遠和爸爸在一起!」老父說不行,於是就坐在旅館的榻榻米上,緩緩地曉以大義(「晚春」、「麥秋」的故事相仿,但人物倒置)。
然而也不能過度渲染這類「大自然」的餘韻,否則又會落入人生如浮雲或浮草式的半禪宗說法。其實小津片中的火車鏡頭更多,火車代表的當然是「現代性」(modernity)。小津沒有川端康成那麼超然,或一味沉醉於傳統的美學境界,小津的入世哲學絕對是基於現代──一種日本式的現代生活,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剛結束的「青黃不接」的時期,「上班族」剛剛出現(「早春」),但上班族住的仍舊是老式的日本房子,所以在這個極有限的空間中,就顯現了小津所獨有的「空白」哲學。
●空間角度
美國評論家──如Noel Burch──往往以此為根據談了不少小津的禪宗式風格。依此類推的話,我們甚至可以把日本人習慣坐在榻榻米上的姿勢也叫作「坐禪」!我認為大可不必。其實日本和中國一樣,飲食起居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儀式,而小津的電影中更注重這種生活儀式,它是一種不斷重複卻不自覺的日常習慣,所以拍攝這種生活儀式時,鏡頭也必須是重複的,不能有任何驚人的視角和和節奏;換言之,務必要求得影片內和影片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致。
小津作品中的這種生活儀式,可以從空間的角度來研究,例如人和物、人和人的對置關係,或鏡頭角度所捕捉的室內空間等等,然而我更感興趣的卻是時間問題。小津的剪接技巧是不露痕跡的,如不仔細看,往往會覺得自己就和那幾個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但讓我自覺的卻是片中的空鏡頭:不但是房中的過道──在人物進入之前的空間──而且是各種其他有關物的鏡頭:街燈、窗戶、衣架、桌子、榻榻米上的床被……,每一個空鏡頭的時間過渡都是有規律的,我曾默默地數過:大概三四秒鐘,不多不少,重複時依然如此。這種重複性的空鏡頭,當轉向人物的中鏡頭時,也仍然保持同一個緩慢──但並不冗長──的速度,這種節奏,如果用音樂的術語就是andante(行板),但非adagio(慢板),我們之所以覺得小津電影的節奏緩慢,是因為看了好萊塢或香港的新片子太多,節奏不是太快就是太不規律,而且無謂的大特寫用得太多!小津的影片中很少有大特寫鏡頭,即使用面部特寫(最接近的特寫也包括整個頭部),它的時間也絕不故意拖長,有時候我會故意數這種鏡頭的節拍,當我本能地運用小津式的節奏說「cut」之前半秒鐘,鏡頭就自然地轉換了。
●平凡生命
這真是鬼斧神工!我久久反思分析,還是說不出一個道理來,試想一部莫札特的「安魂曲」完全用同一個andante的速度演唱出來,或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我當年在新竹中學常聽的音樂)用同一個緩緩的速度奏出,沒有任何重音,而且「完成」了整整四個樂章!抑或是巴哈的cantatas一首接一首的唱出來,用同一個速度,不慢不快、不慌不忙,聽久了可能真會進入「聖樂」之境。(或者會呼呼大睡?!)
小津電影的迷人之處,我認為就在於此。也許我是走火入魔,但入的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小津織造這個世界,用的就是普通人物和空鏡頭。有時他也會越出常規,譬如在「晚春」中他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拍攝片中父女同觀的「歌舞伎」,表現了另一種更「正規」(formal)的儀式,看似與劇情無關,其實用的是小津一慣的旁敲側擊的手法,以此來「反測」男女主角的心態。
走筆至此,才感到我在文中所用的影片例子可能有誤,應該再去查證一次,然而回頭一想又不覺失笑,小津不是和王家衛一樣──應該說王家衛學的是小津──幾乎說的都是同一個故事?因此鏡頭出自何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全部作品中的世界,這當然是一種「作家論」的說法,然而小津這位「作家」呈現出來的世界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飲食起居、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我們也會隨著小津影片中的人物度過我們平凡的一生。
看到這個作者投書 又碰到這兩天剛好是陳金鋒和 la new 熊 要談論簽約事宜 覺得非常捨不得這樣的好選手 居然會淪落到回中華職棒打球 真有莫名的感傷

2006.01.02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10200234,00.html
王建民風 驗證體育國際化
黃國洲
編者按:二○○五年體育風潮盛行,職棒二次涉賭案、首次亞洲職棒大賽,而這其中王建民站穩紐約洋基舞台,該是體壇第一大事。
多年以後,我們這一代的球迷將如何談論二○○五年的台灣棒球呢?
「我想知道那些優秀的台灣少棒選手長大變成怎樣?他們到那裡去了?」這是名人堂投手,三屆賽揚獎得主帕瑪(Jim Palmer)退休轉任球評所講過的話。陳金鋒、曹錦輝可能令他印象不深,但王建民今年的表現應該可以做為這句話的答案了。是的,台灣人,「歡迎來到大秀場!」
其實,曾擔任過多年少棒世界大賽(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在威廉波特所舉行的比賽)講評工作的帕瑪,他親眼目睹的那些選手應該都比這批第一波留美風潮的台灣球員早上幾屆。那些人呢?當年的最佳選項是「打日本職棒」。
台灣棒球的發展腳步向來是亦步亦趨、效法師承的日本,若不是一九九五年野茂英雄赴美刮起「龍捲風」,引發東方球員入侵大聯盟的新浪潮,我們很難想像台灣球員能否有越級挑戰美國職棒的勇氣。當然,外在環境的改變也是一大助力:大聯盟比賽的能見度、兵役制度的革新……
除了共產古巴,世界棒球強權與職業化的關係密不可分,美國職棒肇始於一八六九年,日本在一九三六年成立職棒聯盟,台灣則遲至一九九○年。三國棒球的職業化速度類似等差序列,制度的繁簡也有相當程度的差距(級數、聯盟、分區……),此外,經濟水平也具體反映出此項運動產業的規模。以大聯盟的薪資為例,勞資雙方協議的最低年薪(三十一萬六千美元),對職業化十六年的台灣選手而言,依舊是個令人咋舌的數字。
身為挑戰大聯盟的先驅者,王建民並沒搶到「頭香」(第一位大聯盟的台灣選手是陳金鋒,投手則是曹錦輝),然而,卻無礙他的歷史定位──第一位「站穩」大聯盟的先發投手。而且,最難能可貴的是在美國職棒的看板球隊──紐約洋基,雖說靠著幾分機運,但想要在最勢利難搞的「老闆」(Boss,球團擁有者George Steinbrenner的綽號)、媒體聚焦的大都會及尖刻內行的球迷中脫穎而出,沒有厚實的功夫絕對是辦不到的。特別是他的「沉穩」態勢,稱得上深知棒球箇中三昧──「心智的比賽」。
只要能常保安康,相信今年王建民優異的表現(出賽十八場,八勝五敗,防禦率四.○二)僅是個起步而已,「二年級症候群」應該難不倒這位心智超齡的新秀,只是在好手如雲的大聯盟中,要想長久地佔有一席之地,還有許多考驗在等著他。前洋基名將曼托(Mickey Mantle)就曾說過:「每個打進大聯盟的人,終其一生,都是對棒球有獨特想法的人。然而,從大聯盟的觀點來看,他還是得每樣從頭學起。沒錯,你真的難以相信,花整個生命打球,但對它的理解依然那麼少。」
今年五月開始的「王建民旋風」,對國內的職棒造成兩種效應:樂觀派認為,有推波助瀾之效,可再造棒球熱潮;悲觀的人則以為,眼界大開,高下立判,且好手效法一一出走。兩派意見仁智互見,各有所本,沒料到,在王建民養傷期間,中華職棒竟掀起風暴──球員再度涉賭。
一九九七年首次爆發的簽賭事件,使得國內職棒元氣大傷,二○○三年兩聯盟合併後再出發的中華職棒大聯盟,其實尚處於療傷止痛的過度期,整體環境未見榮景。球迷們用腳投票,就是最好的寫照,偌大的外野觀眾席,稀疏荒涼的景象經常可見。如今職棒再度蒙塵,不但嚇走新球迷,原本三心兩意的老球迷也吃了錘砣鐵了心!第一次是傷心,再一次則是灰心,為何灰心?因為球迷無力!那「有力人士」呢?算了,權力邊陲的運動場上,他們只會錦上「插花」罷了!誰來「主持正義」?笑話,偵辦簽賭的檢察官本身就是個「明牌」包打聽。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一九一九年美國發生「黑襪事件」,大家公認,是兩位救星挽回球迷的心,一位是首任大聯盟理事長蘭迪斯法官(Judge Landis),另一位則是大名鼎鼎的貝比魯斯(Babe Ruth)。二○○五年的世界大賽,「賭」咒纏身的白襪終於洗淨了最後一滴污漬,奪回睽違八十八年的冠軍寶座。而太平洋的另一頭,兩次的放水事件始終沒有救世主出現,一向強調「費厄潑賴」(Fair Play,即公平競賽,此語為民初林語堂所譯。)的棒球運動因而當頭棒喝,懲罰這不知醒悟的國度──年度總冠軍隊伍興農遭提前結束。(十二比一,七局被日本羅德扳倒)。
被視為明年三月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前哨戰,今年十一月的「亞洲職棒大賽」(Asia Series)於東京先行開打。毫不意外,比賽的結局大致反映了各國的棒球實力。阿Q式的信心喊話「坐三望二搶第一」在「不望不搶」的鬆懈意志下,台灣僅贏了「棒球開發中」國家──中國。可是,提前結束的屈辱印記將永載台日兩國棒球史冊。這場難堪的比賽不僅讓許多洩氣的球迷關上電視,更讓明年新球季的台灣職棒增添許多問號。
歲末的台灣球界原本寂寥,卻傳來陳金鋒可能加盟中華職棒的消息,對這位浪跡美職七年的追夢人,回航的計畫使人五味雜陳,假使真成定局,無論如何,希望他多少能發揮一點「貝比魯斯」效應,為奄奄一息的台灣職棒注入一股新鮮的氣息。至少,在政經紛擾多年的這塊土地上,球迷還能有個地方讓心靈得到慰藉。
(作者為棒球文字工作者)




